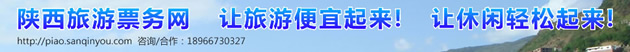| 游遍三秦大地从三秦游网开始>> | 三秦游首页 | 意见反馈 | 天气预报 | 网站投稿 | 上传图片 | 资源搜索 |
艺术阅读推荐:莫奈和他的眼睛
封面
本书是张佳玮所著的莫奈传记,适逢上海莫奈特展,印象派的欣赏热潮又会兴起,书展相互辉映。 张佳玮是目前知乎和豆瓣上美术史知识文章阅读量最大的作者,并于法国巴黎攻读古典艺术鉴赏,所著作品史料丰富可靠,图文并茂。本书立足于莫奈当时生活的十九世纪法国艺坛,将影响了印象派产生的浪漫主义、巴比松画派等和当时反印象派的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矛盾生动复原。本书提到很多莫奈 不为人知的小段子,例如与雷诺阿蹭饭吃,装大腕骗车站站长提供写生产地,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为一体,表现莫奈大师之外的面貌。作为普及性质的作品,不了解西方艺术和梵高的读者也可轻松阅读本书。加之篇幅精干,怯于长篇的莫奈传记的读者,可以从本书入手了解这位大师的生平轨迹。后续张佳玮创作的伦勃朗传记也即将上市。
作者简介
张佳玮,生于无锡,后居上海,现住巴黎。自由撰稿人。主要作品有《朝丝暮雪》《再见帕里斯》《瞧,科比这个人》《无非求碗热汤喝》及《代表作和被代表作》等。
内容简介
满肚子文人段子,爱掉书袋的张佳玮,首次将擅长的传记笔墨与熟读的美术史料融为一体,书写印象派创始人莫奈的一生,把画家重新镶回印象派诞生之初的法国,复原塞尚赞叹的“那是一双多么美妙的眼睛”所看到的“麦垛,鲁昂的教堂,拱桥和睡莲,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
精彩看点
◎适逢上海莫奈特展,书展相互辉映
◎莫奈传记中最亲民版本,最生动讲诉
知乎豆瓣上,艺术史最受欢迎作者张佳玮,首次将自己擅长的传记笔墨,与熟读的美术史相结合,写出十九世纪法国艺坛的大背景和莫奈人生的小细节。
◎图文并茂,普及阅读佳品
【目录】
第一章 少年
1 眼睛
2 那个叫小奥斯卡的孩子
3 欧仁·布丹
第二章 巴黎
1 世界的模样
2 朋友与师长
第三章 “新星”
1 落选者沙龙
2 户外作画
3 卡米耶
第四章 突破
1 困境
2 “你还是去荷兰吧!”
3 《日出·印象》
第五章 印象派
1 命名
2 革新
3 船上的莫奈
第六章 战斗
1 圣拉查尔车站
2 亡妻
3 分裂
第七章 新时代
1 后来者们
2 联画
3 吉维尼的莲园
第八章 “克劳德·莫奈和他那个花园”
1 生而为画者
2 那双眼睛闭上了
3 20世纪
【试读】
眼睛
“他只有一双眼睛,可那是一双多么美妙的眼睛啊!”
——保罗·塞尚
1926年12月5日,诺曼底的寒冷冬日空气,折磨所有人的肺。吉维尼小镇上,某个房间,一双眼睛眨了眨。没人知道那时候,这双眼睛还能不能看见东西。
然后这双眼睛合上了,再也没有睁开。
许多学者认为,这双眼睛最后还能眨动的那些时光,已经看不清人间的景色。证据是,十四年前,这双眼睛已经得了退化性白内障,一度濒临失明。三年前,这双眼睛经过了两次手术,得了黄视症,所看到的一切都格外泛黄;随后,上帝恶作剧似的,让这双眼睛犯了紫视症,望见的世间万物,都被紫色渲染。所以,最后闭上之前,这双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颜色,没人能知道了。
这双眼睛闭上这一年,1926,世界艺术正进入一个狂欢时代。这一年,马格利特快要完成他的《受威胁的凶手》,全面体现他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奥德出版了《荷兰建筑》,开始总结阿姆斯特丹派与鹿特丹派的成果;格罗皮乌斯在《艺术家与技术家在何处相会》一文中说:“物体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一切东西必须在各方面都同它的目的性相配合,就是说,确实能够完成它的功能,是可用的、可依赖的、便宜的,也是合理的。”亨利·摩尔开始以墨西哥玛雅文化中托尔特克神庙大门口的雨神雕像为原型,创作《斜倚的人体》;伟大的毕加索于十年前结束了自己的立体主义时期,开始试图玩超现实主义;亨利·马蒂斯早在二十年前就玩腻了他的野兽派风骨,正把他的不朽才能推广到雕塑、壁画、插图和版画方面。
那是个伟大的年头,20世纪只过去1/4,但艺术家已经打起了他们的旗帜:他们不满足于简单地表现“他们的所见”。他们几乎反对研究自然形象。大多数批评家们已经相信了这一点:唯有最彻底地摆脱传统,才能带来进步。
但在这双眼睛初次看见世界的年头,却并非如此。那是1840年,这双眼睛初次看见巴黎的天空。那一年,德国画家帕斯卡尔·弗雷德里希谢世。而此前三年,英国史上最好的风景画家之一约翰·康斯特布尔过世,与他齐名的威廉·透纳则在公众的一片不理解声中,认真地画雨水、蒸汽和雾霭,并谋划去瑞士风景佳妙处,做他钟爱的水彩画。在法国,伟大的让-奥古斯特·安格尔已经完成了新古典主义的丰碑,正在广纳门徒,营造学院派美术的壁垒;而“浪漫主义狮子”欧仁·德拉克洛瓦则在狂飙突进,他已经画完了《肖邦像》和《乔治·桑像》,他已经完成了《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他正在竭尽全力嘲笑安格尔的“线条即是一切”,一边在他的画里任笔触挥洒如长发,一边怒吼“色彩即是线条”!
在1840—1926这漫长的86年间,这双眼睛见识了多少事呢?无人能够真正得知。能够用来做证据的,是这双眼睛曾经端详过的一些画,一些风景。这双眼睛曾看着一双手涂满了无数画布,最后在角落里署名,这双眼睛主人的名字:
奥斯卡-克劳德·莫奈。
户外作画
1863年底,莫奈和巴齐耶跑去了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画那里的橡树和石头。他几乎从此抛弃了画室,日日在此流连。不久,雷诺阿和西斯莱作别了格莱尔画室,跑来与他俩扎堆。马奈的成功给了他们信心:不必去在意细部、阴影、对比,用快速笔触,在户外完成一切。
他们不是第一拨在户外作画的人。1857年,巴比松画派的杜比尼就开着一艘小船——他命名为“博坦”——浮河作画。同样的年份,布丹在诺曼底海岸吹着海风作画。但是,他们多少脱不了前辈套路,总得留一些工作在画室里完成,而无法完全在户外,从头到尾完成一整幅画。
对莫奈来说,他的问题已非铅笔、水彩、色粉的选择,他也不愿意在户外画出草图,再跑回画室细行加工。他接受了容金德的指导,重新看清了世界的色彩;他一直被布丹鼓励,说“当场完成的画最有力量”,而他走得更远:
他要急速地表现自然的某个瞬间,离开画室那些明暗遮挡的光线,带着小幅画布和油彩管,来到阳光下绘画。只要当场完成,哪怕如马奈那样,承受“这幅画没画完吧”的质疑。莫奈不相信一切既定规则。他学习了库尔贝、柯罗、布丹、容金德,但又不全然相信他们。他最后相信的,只有自己的眼睛:
“依据个人的印象,而非借用普遍感受的规则,来完成绘画。”这是他的理想。
1861年,他完成过《画室一角》,那是幅精致和谐的油画。1862年,《猎人的勋章》,他对色彩的和谐有了进一步体会。但他没到此为止。他需要更多的户外光线。他在自然里行走,看见橡树、行云、河水与风,以及无时无刻不让他目眩的阳光。这些不是安格尔一派要求“去美化现实”的事物,而是户外阳光制造了完美景色。他信心十足:
“一个人能够画出他所见到和了解的东西,靠观察和思考来活下去。”
因为,一如他对巴齐耶感叹的:
“我每天都发现越来越多美丽的东西。”
那时节的年轻学生,穿衣打扮大多是波希米亚风——换句话说,吉普赛人似的,以不羁为美。但雷诺阿后来描述说,莫奈的打扮却很布尔乔亚情调;虽然穷困,却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他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却要穿花边袖子,装金纽扣!”在他们穷困期,这衣裳帮了大忙。那时学生吃得差。雷诺阿和莫奈每日吃两样东西度日:一四季豆,二扁豆。幸而莫奈穿得阔气,能够跟朋友们骗些饭局。每次有饭局,莫奈和雷诺阿两人就窜上门去,疯狂地吃火鸡,往肚子里浇香贝坦红葡萄酒,把别人家存粮吃罢,才兴高采烈离去——雷诺阿后来对他的女儿说:
“那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
年轻的血气足以弥补一切,所以那时节,莫奈很是自豪,常自夸自赞“画画时从来不去思考任何一个画家,模仿任何人的风格”。但自我赞美到底没法换钱。为了谋生,他托巴齐耶卖画,未遂。马奈的画已经够离经叛道,让买家望而却步,何况比他更激进的莫奈?
1865年初,莫奈和巴齐耶在同一间画室里劳作。他渴望画出一幅类似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般的作品。那年春天,他画得发了疯,几乎错过了新沙龙的消息——1865年的沙龙,与以往不同。马奈和库尔贝依然被当作荒诞的激进派被嘲笑,但逐渐有了话语权。巴比松画派也占据了前台。两年之前的落选者沙龙,在官方而言是闹剧,但多少也让上头明白过来:是得换换思路啦!
1865年的沙龙评审委员会,只有1/4的成员是“上头的人”,归当局划定;剩下3/4,民主选举,由画家们推选。官方此举虽有假施仁义之嫌,但也算广开言路。在许多传说里,最戏剧性的故事是这样的。1865年沙龙开幕当天,马奈刚到,就被人围上,没头没脑的赞美:
“这海景,画得真好!”
马奈惊诧了:“我没画啊?!”
一个误会:马奈(Manet)和莫奈(Monet)两人名字,仅差一个字母。两年前马奈已声名赫赫,而莫奈还是个无名小卒。众人看了莫奈笔触雄浑有力的画儿,匆匆瞥一眼作者名,理所当然地想:“这准是马奈的!”
这是莫奈成名的开始。评论家保罗·曼菲认为莫奈很诚恳,《美术公报》上如此陈述道:“一个新名字必须被提及。我们还不太认识莫奈先生,但我们可以看到那两幅画。《勒阿弗尔海角》和《鸿弗勒尔的塞纳河口》。这些画看上去还像初学者作品,缺少长期系统学习所拥有的细腻技巧。但对色彩和谐的审美、对明暗层次的感受、令人感动的整体效果、显著的强度、看待对象的大胆眼光,这些资质都在展示莫奈的无限可能。我们将会满怀兴趣,追随他的画作。”
如今,你依然可以从他的《勒阿弗尔海角》里,看到布丹与容金德的影响:那层次多样、光影重叠的云彩。而《鸿弗勒尔的塞纳河口》,波浪与云影令人震惊,而对船的描述,多少让人想起英国人透纳。评论家那时已经注意到了莫奈的特色:“和谐的色彩”,“前景里水与云的笔触颇为大胆”。
这是他初次的成功,但莫奈刚在巴黎获得赞许,立刻回头,继续去枫丹白露,去鸿弗勒尔,完成他的野心之作了。他想要一幅《草地上的午餐》那样的大作,想融汇自己一切的技巧和想法。
25岁,莫奈已非初来巴黎时,那个对库尔贝五体投地、说啥听啥的青年。他依然赞叹库尔贝娴熟从容、随心所欲的用笔和调色刀,依然钦服于库尔贝对宏大原则的强调;库尔贝澎湃到近乎粗放的笔触,尤其令莫奈赞美,但只有一个细节让莫奈不快:
库尔贝,与许多画家一样,习惯在暗画布上作画——他习惯把画布抹上褐色,以便控制光与色块。这习惯真不算新:18世纪,克劳德·洛兰这样的风景画家,已为后代画家总结出许多口诀与法则,可以称作为“业余绘画爱好者流水线”。其中要务之一,就是配色法:前景中当涂暖色,最妙的莫过于棕褐色或金黄色调,背景应该褪为淡蓝色彩。
当然,这法则也不是人人都遵守。比如英国风景画家、德拉克洛瓦为之喝彩的康斯特布尔,对这套老八股甚为厌恨,从来都拒绝在前景涂上那“古老小提琴一般柔和的棕色”。传说中,康斯特布尔有位朋友抱怨他:怎么不给画先涂上小提琴色呢?康斯特布尔递过一把小提琴:“睁开眼睛看看吧,小提琴的颜色真是这样的吗?”为了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康斯特布尔酷爱到乡间去做写生速写,然后回画室做细心加工。
对莫奈来说,他比康斯特布尔更进一步:他不想要一切预定的效果,拒绝古典的、雍容的、不会出错的褐色。他要用白色的画布,来描绘蓝天、白云、绿树。他要亲自一点点勾勒明暗层次,他坚持在户外现场,完成一切绘画,而不是回到画室,再做别样的加工。总之,他让自己的眼睛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对库尔贝影响的敏感,让他有些自我烦恼。他已经决意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但多多少少,布丹、容金德、柯罗和库尔贝,都在左右着他的情绪。这像一种奇怪的悖论:莫奈师从的这些人物,都是些天才的革新家;他们都在鼓励莫奈,抛弃一切影响,拒绝跟从任何人;可是,对革新家们的遵循,会成为另一种跟随……在彷徨无计中,莫奈的目光看到了另一个人:1865年3月,这个人走进了他的生活。
那是个来自里昂的姑娘,卡米耶·唐秀,小莫奈七岁,这年不过18。她生得美貌,来到巴黎,是当模特来着。
20世纪
印象派那一代人,大多在20世纪到来前后,被召唤进了时间的黑暗中。卡耶博特、西斯莱、毕沙罗、凡·高、高更、塞尚——他们倒在了19世纪最后十年,到20世纪前六年。他们大多没来得及品味20世纪,没来得及亲眼看见这风起云涌的岁月:流派和主义在20世纪的前十年纷至沓来。比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比如马蒂斯的野兽派。高更至死都爱着他的荒岛。抽象、表现各类主义在一路抽芽。曾经是新人的修拉已成过去式。
实际上,20世纪的艺术家们,经过19世纪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叛逆后,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莫知所从。19世纪的造反者们——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然后是莫奈和雷诺阿——打算把古典程式全部清除出去;当障碍一一排除之后,印象主义者的确做到,可以把视觉所见准确绘在画布上。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西方整个传统的抛弃。凡·高、高更和塞尚们,所做的就是这个:20世纪的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独创性。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复习大师的技艺了,他们得不断创造新的主义。实际上,离20世纪还有十年就逝世的凡·高,早就明白了这点。后来的一代画家,不是不会画“正确的肖像”,只是:
“我夸张头发的金黄色,我用橘黄、铬黄、柠檬黄,而在头部的后面,不画房间的普通墙壁,我画无限(the infinite)。我用调色板所能调出的最强烈、最浓艳的蓝色画了一个单纯的背景。金黄色放光的头衬着强烈的蓝色背景,神秘得好像碧空中的一颗明星。哎呀,我亲爱的朋友,公众只能认为这一夸张手法是漫画,然而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命运的玩笑。莫奈们那些“尽力还原眼睛所见一切”“抛弃一切已有技巧”的画作,曾影响了凡·高;但凡·高们走得更远后,就不再以“还原所见”为宗旨了。莫奈们战斗的矛被传授给了后代,但后代并不全盘照搬——或者说,后代承袭的,仅仅是莫奈们不朽的精神。
也许印象派最伟大的胜利,是制造了这么一个不朽的例子:再怎么遭遇非议的艺术家,某天都可能获得尊崇。19世纪60到80年代,那漫长酷烈的战争,那些穷愁潦倒的艺术家,有些人没能挺下来,比如年未四旬就过世的凡·高,比如在普法战争里死去的巴齐耶。但是20世纪到来时,莫奈、雷诺阿、毕沙罗、马奈们,这些曾经被当作妖怪、叛徒、流氓、骗子的人物,都获得了国际级的名誉。
莫奈和雷诺阿是幸运的:他们活得足够长,他们来得及在活着时就享受胜利。他们亲眼看到自己成为经典画家,他们的作品被政府买下,或被收藏家追逐。这未必能弥补他们早年所受的贫穷冷遇,但当初以“高贵的画风”“平衡的构图”“正确的素描”攻击过他们的人们,到此终于可以闭嘴。经典美术的陈腐俗套被他们彻底踩倒。这件事永远改变了批评家和艺术家们的地位对比。评论家们的威信遭到损害,再未恢复。所有艺术革命家自此以后,都会把莫奈们的斗争当作传奇。每当公众对他们的革新手法有所异议,他们就可以来一句“当年莫奈和雷诺阿也是这么被批评的”,然后可以很自傲地坚持下去,而且相信,时间会将应得的冠冕还给他们。
就像,在莫奈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时间把应得的冠冕,还给了他。我们足够幸运的是,世上有过奥斯卡-克劳德·莫奈那么一双独一无二的眼睛。这双眼睛无法判定历史的反复无常,判定舆论的朝令夕改,判定他的名字会在多年之后,被评论家、心怀大志的青年画家和收藏家们怎么评论。但这双眼睛如此敏锐地占有了那个时代,所看到的一切:诺曼底的海,卡米耶,阿让特伊,塞纳河,吉维尼,伦敦,威尼斯,荷兰的赞丹镇,他的船,他的麦垛,鲁昂的教堂,花园,拱桥和睡莲,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他看到了,并用他的大笔点石成金,给这一切赋予了灵魂。于是在他死后,19世纪的阳光和灵魂,依然透过那双捕获一切、唤醒一切的眼睛,活在我们所见到的世上。
编辑:秦人
关键词:库尔贝 巴比松画派 德拉克洛瓦 Manet 格莱尔